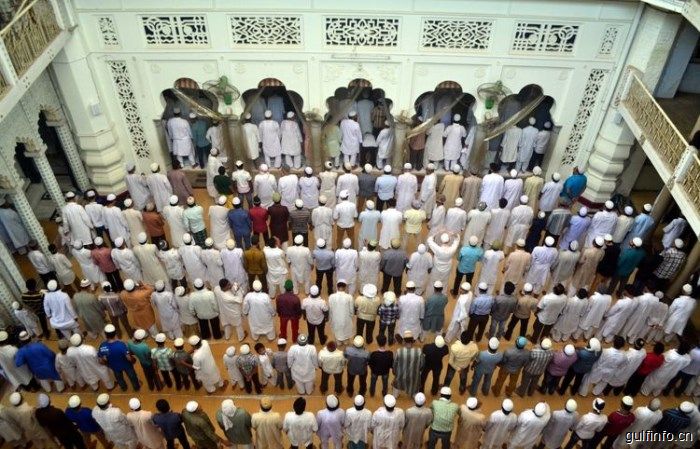“其实肯尼亚人对中国的心态很特殊,因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比我们好!”一位在非洲呆了十余年的老媒体人,在谈及中肯之间的不爽时,做了这个评论。...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已经算是“小老肯”的我,被所在小区一个新来的老弟好奇地莞尔了一下:
“我一直想问个问题,是不是来非洲的都是在国内混的不好的?或者混不下去的?”
这孩子刚来不到一个星期,就问了这么个尖锐的问题!一想到自己也属于“来非洲的”,心里就有点小沧桑。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很典型,它折射的是国人对于非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认识。
对于国内多数民众而言:
第一、非洲是无一例外的蛮荒之地,落后、野蛮、外加危险(战乱、瘟疫或者恐怖袭击);
第二、来非洲的人如同满清时代的小辫子留学生,在天朝没了出路,只好去蛮荒之地讨生活。
但是,在淘金者眼里,在面临激烈竞争的政治家眼里,非洲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充满机遇的大陆,是国际强权政治角力的联合国票仓:
第一、非洲是当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陆,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中国过剩产能、资本、技术、劳动力的理想“接盘侠”;
第二、中国正在积极履行对于非洲的“负责任大国的义务”。用当下最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授人以渔”的潜台词,挑明了中国与非洲的另一种关系:一方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另一方则是充满求知欲的学生。但是,很多来自中国的普通“老师”却没有感受到学生对于老师的应有尊重:
“我们来这里投资,教他们如何管理,给他们工作,为什么他们并不感激我们?反而处处刁难?”
“我们给他们修建了道路、住房、桥梁,他们怎么从不知道感激?”
“他们的官员和警察就知道讹中国人的钱,不贿赂什么事都干不成!”
生活于肯尼亚,经常会听到同胞们类似的抱怨。很多人会归因于本地人“不知感恩”、“好贪小便宜”等“国民劣根性”,这种想法很有感染力,因为,但凡与外人起争执,把“不是”都推之于另一方,是自我解脱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这种解释无非是另一种精神胜利法,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一位专门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简单定性,“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大量存在类似的现象。”
于是,我想起了作家流沙河讲述的关于抗战时期成都农民跟驻成都美军飞行员的“猫鼠故事”:美军飞行员的高大上待遇,跟1940年代川中农民的日子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于是,成都农民对美国大兵也竭尽坑蒙拐骗之能事:受命给美国大兵炖鸡汤的农民,会把整只公鸡放进泔水桶里带回家,或者自己享用或者拿到集市上换钱,给美国兵留下“纯正的”汤;美国大兵夜晚脱放在门口的皮鞋、皮带、长裤之类,第二天就会被当地人摆放在军营门口的自由市场上出售;附近居民甚至会偷偷卸下美军战斗机机枪子弹底部的铜圆环,只是因为废铜可以马上换来现金。总而言之,如果把主语换掉,很多人乍一看,恐怕会以为这是今天发生在非洲的故事。
流沙河这段亲身回忆,印证了古人的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穷重压之下的普通民众,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在什么时代,恐怕都是共同点多于不同点,所谓“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所以,该反思的似乎不是被我们所嘲笑的穷人穷国,似乎更应该是我们自己:也许今天我们之于非洲,更类似于1940年代的美国大兵之于成都郊区的农民。
“其实肯尼亚人对中国的心态很特殊,因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比我们好!”一位在非洲呆了十余年的老媒体人,在谈及中肯之间的不爽时,做了这个评论。
这句话是言之有据的。今年夏天,在蒙巴萨参加一个媒体会议时,我亲耳聆听了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先生自曝自己与非洲的几宗最:第一宗最,李肇星先生第一次使用空调,就是1960年代在肯尼亚的蒙巴萨;第二宗最,是肯尼亚人教会李肇星先生驾驶汽车的;第三宗最,李肇星先生甚至说自己的英语,都是在肯尼亚得到显著提升的,以至于迄今都带有明显的“肯尼亚口音”。这就很明白了:曾经有“东非小巴黎”之称的肯尼亚的确曾经比中国阔气过----我还记得,我们家安装的第一个空调似乎也要到1990年代了!
但是“大地像陶轮一样转了起来”:今天的中国与非洲,彼此不再是昔日那对蓬头垢面的难兄难弟,而是一个已跨入先进,一个依然落后;一个已经富足,一个依然贫穷;一个已经周游世界,一个依然只为明天的早餐发愁。换句话说,当我们已经以老师身份出现在当年的兄弟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问一句:是我们变了?还是对方更不中了?
有一个变化比较明确:我们已经以老师身份出现在非洲大地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老师与学生应该属于人伦关系中最和谐、最易相处的的关系之一。但是,真相其实往往出人意料:在国际社会中,老师与学生,其实是最纠结、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一种情况是霸道老师欺负幼弱学生,比如前苏联与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开始模仿前苏联探索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苏联这个老师经常欺负学生:先有斯大林与蒋介石政府交好而同时有意疏远中共;再有斯大林“不许中国革命”,企图劝阻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接着毛泽东首次访苏就坐了近一个月的冷板凳;然后就是苏联断绝给中国的援助、中苏论战、中苏珍宝岛之争;最后发展到1970年代末到苏联解体前,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联合制衡苏联的奇妙局面。这是国际精武门:中苏同出一门,但是却睚眦必报;中美本是江湖冤家,却能惺惺相惜----霸道老师欺负学生,导致聪明的学生结了外援来抗衡以致拖垮了老师。
一种情况是学生出息了欺负老弱的老师,比如中日关系。古代的东亚,中国与日本如同一对师生,基本上保持了“长慈幼教”的正常师生关系:从先秦徐福东渡扶桑的传说,到大唐鉴真和尚的六次东渡,中国的文化典籍,被日本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但是到了近代,中国老朽没落了,于是日本这个学生转投了西方的强壮老师,长了本领后一刀接着一刀毫不含糊地捅向曾经的老师: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件”、“七七事变”,几乎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屠杀凌辱千百万普通中国人,中国人记忆之惨痛,以致到现在中日民众间互相仇视的心态还很常见。
那么今天的中国“老师”,面对非洲“学生”的时候,两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师生关系呢?
的确有点纠结。因为仅仅在20年前,我们的报纸还在大声疾呼“亚非拉兄弟是一家。”中国对非洲最富有感情的一句话是:“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当年大家都是街头打架混吃的好兄弟,今天一个发了,一个依旧穷得叮当响。穷兄弟蹭点吃、蹭点喝的,似乎也无可厚非吧?其实中国政府是挺念旧的,2015年一口气就宣布了600亿美元的对非专项援助,着实让非洲各国政府兴奋至今,各大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开工。
问题依然出在民间。这个问题跟中国的问题有点类似,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切实增加基层民众的“获得感”,让绝大多数民众能切实“分享改革福利”。在非洲,问题也一样:要让普通民众更多分享中国援助的福利,也要切实增加普通民众对中国援助的“获得感”。
这是一个很复杂、很煞费苦心的系统工程,似乎普通人难以着手。但是每一个行走非洲的普通中国人,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做的。因为当老师么,普通中国人得有老师的修为吧?
回到上面成都农民与美国大兵的故事,流沙河先生在回忆这个故事的时候,尤其重点指出了:当年那些美国大兵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当地居民的各种小伎俩而动刀动枪,甚至也没有动过怒。这是一种强者的宽容,当老师了,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包容意识?
缅甸最近和美国走得很近,美国人在“亚太再平衡”的口号中重新回到了这个佛教之国。缅甸一个高官在谈到对美国人的感受时,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美国人对缅甸人真的很尊重、很平等。”
弱国无外交,缅甸想在外交角力场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只能是痴人说梦。所以我想这位缅甸高官其实想说的是:在民间交往中,美国人对缅甸人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其实这恰好似乎是中国人,普通中国人缺失的地方: 在人际交往中较大范围内存在对当地人和当地习俗的不够尊重。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就缺乏平等的基因,一贯是物有好坏优劣,人分三六九等,人们习惯于对强者示好,对弱者示威。所以不得不再啰嗦一句:一切外在的问题,都应该从内部来克服,首先学会平等对待自己人,然后才能真正平等对待外面的人。师道尊严,无外乎一视同仁?
所以,对于篇首的问题,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能平等待人了,自然就内心平和了。